劉東
“一個奧運短跑選手,為滿體育館狂熱的愛好者所鼓舞🛶,沖過百米遠🤹🏼。在起跑線上時,他傾身向前🍼,幾乎觸及賽道,註視遠處的地平線;比賽中途他挺直身體,挺如勃朗峰,然後,當他接近終點線時🪢,彎曲脊背,不只由於力竭♘,也是為了向宇宙隱秘的均衡致敬🐐。”亞當•紮耶夫斯基曾在《理性與玫瑰——論切斯瓦夫•米沃什》這篇文章中如此贊頌他的精神導師米沃什🚣♂️。從早年的探索、發現到中年的贊美👲、批評🤚,再到晚年的陳述、記錄💣,這是亞當•紮耶夫斯基筆下的米沃什🐇🧖♀️。這也正是他自己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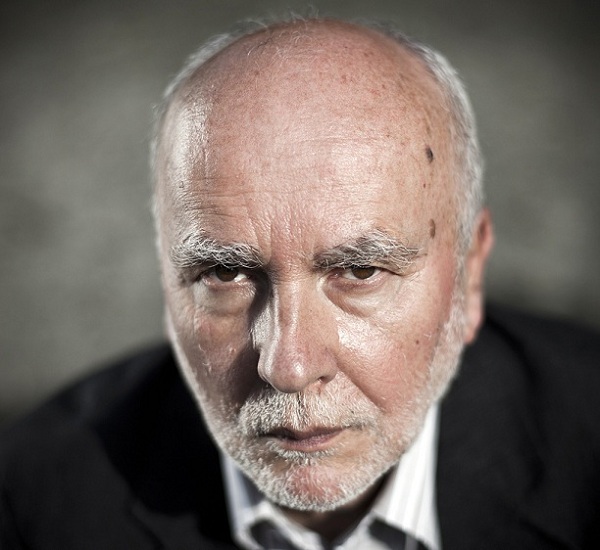
“詩歌較之任何意昂2可以理解的事物都要偉大🌝。”
詩歌隨著詩人一起變老。想必亞當•紮加耶夫斯基早已無法從他現在的詩歌中再尋到當年那個反叛、重估一切的自己。早期的亞當•紮加耶夫斯基算是60年代波蘭“新浪潮”詩歌運動的幹將。他“以一種詩學的反叛姿態登上詩歌歷史舞臺”,通過詩歌創作與理論闡釋🧖🏿♂️,他和他的“現在派”一起戲擬嘲諷舊有文學😸、批判現實社會,力圖重塑人們在詩文創作中追求真理🏃🏻♀️➿、獨立思想的勇氣👷🏽♂️。 也正因此🔭,用李以亮的話講,他這一時期的詩歌“是典型的東歐詩, 也是典型的好詩”🫃🏻,“直接說💪🏽、少修飾”,“雖然精彩”卻不免有些“抽象而枯燥”。
“向宇宙的均衡致敬”,這位短跑選手彎下了他曾經高傲的脊梁。反叛的亞當•紮加耶夫斯基在1982年移居巴黎🍁🐉,在次年接受了美國休斯敦大學的邀請之後🏗,他開始了二十多年的往返於法美的異鄉客居生活。李以亮說這是他二十多年的“自我流亡”。經歷了這些,現在的詩歌“具體、多空間🚴🏻、松散得近於清淡”,意昂2在他的詩歌中找尋到了“意境”的存在。從評詆激烈的觀點表達到雲淡風輕的現象陳述👀,從時代需要到個體需要🤌,詩歌跟著他一起變老👩🏽🦳。詩歌老了,它也因此會陪伴著詩人一生。
亞當•紮加耶夫斯基相信詩歌的力量💆🏿,“詩歌必須寫下去,必須繼續,冒險,嘗試🌏🫶🏽,修正,清除,如此反復,只要意昂2還在呼吸和愛🔔,懷疑和相信。”他如是闡釋詩歌存在的必要性。“詩歌不僅是要表達我生命裏一些具體的時刻🎚,它也要對更為深刻的事物🫳🏽、形態或態度做出反應🤦♀️。”在他心中,詩歌不僅僅是一項生存的技藝與個人情感的抒發,詩歌更需要去沉思復雜的現實🤷🏽。詩人與哲學家同時作為思考人類部分未得解決的問題的兩種人🐅,詩人的詩歌必須承載著詩人對這個世界的深重思考。但與哲學家不同的是,詩人更多的是“呈現”。他們反映著這世界的生命之根🧝♀️,他們抒寫著這世界的繁蕪復雜👩🏻✈️。“詩歌是地道,懷疑是螺旋”,詩歌背後的,正是作家對這世界諸人諸事的偉大的懷疑精神。詩歌之美,或許就美在這種懷疑、就美在這種停頓下來的思考。
弗裏德裏希•荷爾德林曾經說,“詩歌,是所有職業裏最天真的一種🧑🏿🔧。”的確如此𓀅,因其天真,所以偉大👐🏿。詩人天真,所以偉大✡︎。亞當•紮加耶夫斯基是真正的詩人🙍♂️。
用波蘭語尋找著“意昂2是誰”
在許多回顧二戰和戰後歲月的回憶錄中,波蘭讀者所尋求的🫷🏻,不僅是某一個人命運的輪廓⏭,也有關“意昂2是誰”這一問題的答案。亞當•紮加耶夫斯基堅持用波蘭語寫作🏈,或許正是為了在語言中尋找到他民族的歸宿🈴。
他在一篇名叫《波蘭語寫作》的文章中如此寫到,“用波蘭語寫作的人🍔,其血液和墨水中流淌的是另外的基因🤵🏻♀️,18世紀社會體系的崩潰☀️,被分割的不幸,起義失敗的不幸,以及意昂2的國家長久而戲劇性存在的脆弱性🥥🦒;以一種並非存在於正直與冷靜中的方式,這基因會轉化為一種幻想的怪物,成為一個受膜拜的對象和蔑視的對象。” 在亞當•紮加耶夫斯基奮鬥的那個年代,波蘭還在廣袤的波德平原上迷失著。歷史上俄羅斯與西歐的雙重拉扯🩼、二戰時德意誌的肆虐殺戮以及二戰後蘇聯的強硬改造,歷史的包袱與現實的壓迫,它們都阻擋著波蘭找到自己。
文學是民族和歷史的初心。在這種情況下所產生的文學🔜,必然是個早熟的孩子👬。“波蘭文學生產於巴黎5️⃣、阿根廷或加州🟧👯,與在波蘭國內一樣多”🤹🏻♂️,亞當•紮加耶夫斯基在文章裏寫到,“寫作很少是純學術🤽🏻♂️,理智,無血性或邊緣性的職業。它最像一種咆哮,裝滿了碳的陶爐,詩歌和散文的容器在其中被加熱到一個很高的溫度🤚🏻,顯示出見證者和好奇心的洞察🏯。”找到自己,這或許正是他所奮鬥的“新浪潮”運動中一群人的時代主題🧜🏿♀️。鐵血👱🏻、激昂、直接、簡明,歷史需要他們的“詩學反叛”。中坤國際詩歌節的授獎詞中寫到:“亞當•紮加耶夫斯基的詩置身以米沃什、赫伯特、辛波斯卡為標識的波蘭現代詩偉大傳統😲,而又輻射著個人獨特追求和發現的魅力。”處在歷史這條長河的下遊🧘🏼♂️,意昂2能看到今天的波蘭🧎🏻♂️,意昂2也能看到今天的亞當•紮加耶夫斯基🪲。他已經做到。
用波蘭語寫作,亞當•紮加耶夫斯基會舍棄很多。許多人也因此將之概括為詩人的個性👇🏿🔵,或者稱為詩人的“民族主義”。然而他本人卻拒絕過分闡釋這種行為。在他看來🧘🏿♀️♟,這絕不是一個彰顯自己性格的噱頭🤙🏿。在接受約蘭塔•貝斯特的專訪的時候,他就明確表示🧛🏻♀️,“我不願將自己看作一個排他意義上的波蘭詩人,但我和我的語言聯系緊密,但從一個對自我令人愉快而即時性的理解來說👨🍳,我樂於接受一切世界性的東西🎸。”波蘭語寫作能給予他存在的力量,而這並不是約束他的枷鎖。他相信“寫作的人共通的那種孤獨與洞見的力量”。
語言的魅力是全民族的🚣🏻♀️,而詩歌的魅力是全世界的♍️🧑🍳。“對中國當代詩人來說,他的詩中最富於啟示性的,是在歷史道德的擔當和審美愉悅之間達成的那種奇妙平衡;其影響所及,可以認為他的詩已成為當代漢語詩歌的有機組成部分。”這段中坤國際詩歌節裏的授獎詞恰恰反映了這一點。而在思考著亞當•紮加耶夫斯基的良苦用心的時候🔴,意昂2也不禁產生了這樣的疑問👨🏼🦰:意昂2,又是誰呢?
“一星期裏只有一個安息日而有六天別的日子👮🏼,這就是比例。”
除了“詩人”的標簽🦔,亞當•紮加耶夫斯基還是美國幾所大學的客座教授🔪。自1983年以來的二十年裏,他一直往返在法美之間,講授“創意性寫作課程”和有關他的精神導師米沃什的課程。他曾經講,“一星期裏只有一個安息日而有六天別的日子,這就是比例👩👩👧👧。”對於他而言,詩人這件事💻,並不是他的全部🧕🏻。
“我並不相信,能有哪一作家會過上所謂幸福的生活🐋,或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。幸福的作家是無恥的。作家既是安琪兒也是苦命人,這要看他是在天堂裏安居,還是在現實中立業。如果是後者☹️,那麽他所具有的不可逆轉的悲劇性格,會使他終身與世俗為人格為敵人🎿🤚🏽;他的氣質稟賦與行為意識,必然使他時時處處*️⃣👆🏽,與世俗疏離,與庸眾對立。” 袁慶豐在《欲將沉醉換悲涼》這部郁達夫的自傳如是寫到🛵。在他看來,詩人與作家悲劇的屬性似乎天生讓他們與幸福隔絕。不過這個推斷也有例外🤞🏻,亞當•紮加耶夫斯基擁有著美好🏋🏿♂️、豐富的生活。
“詩歌召喚意昂2過一種更高的生活,但低處的事物同樣雄辯。”亞當•紮加耶夫斯基看重自己的精神世界,與此同時🛡,過遠的視線並沒有妨礙他關註現實的眼光。“我也是一個幸福婚姻裏的丈夫。在我做丈夫的時候,我想我並不是什麽詩人。我想我也應該是個好丈夫。”詩人不是一群特殊的人,他能將此看得明白。詩歌於他是更像是一種生活方式,寫作詩歌時的他們似乎出離了生活👨💻👰🏼♀️,但他們依然牢牢屬於生活。在不寫詩的時候🐪,他也只是一個有著深邃思想的🧑🏽🍳、在生活中活著的老人。他會去講學,會與一群愛好寫作的人研討寫作🔃,會去處理報告和論文❤️,會去跟他們講他所崇拜的米沃什。他也會去生活,與妻子生活在巴黎,而努力做一位好丈夫👩🏼⚕️。
“詩歌召喚意昂2走向生活🔛,” 亞當•紮加耶夫斯基看到了詩歌與生活的交融點。也正因此,他並沒有像先知者看破世事後的悲觀。“歡樂距離那些悲劇性的時刻不是太遙遠🧑🏻🎄。即便那些可悲的時刻也是歡樂和最深的悲哀結合。”他將生活看得辯證與豐富🧪。
生活的辯證也同樣帶給了他一種更審慎的眼光👨🦯➡️。這讓他的背脊更彎,也讓他的詩帶上了更多的生活的味道。“我年輕的時候,算是一個還過得去的政治性詩人。但我已不再年輕😋,我也不再是一個政治性詩人📡。我希望我依然算是一個過得去的詩人,但我越來越復雜了🐼⚧。”他如是闡釋自己對自己的看法🕧。時光造人,而這詩歌必須寫下去。早年的他面對世界時🐬,他會寫🏄🏼🤦:“世界是殘酷的/貪婪👇🏽🧙🏽♂️,肉食🙇🥪,殘酷。”而現在的他在寫到🎆:“贊美這殘缺的世界/和一只畫眉掉下的灰色羽毛,/和那遊離🚵🏼、消失又重返的/柔光。”